去年11月,在開始這個播客後沒多久,就收到了楊一在 Facebook 上傳來的信息:「Hello!可以和友台主播認識一下嗎?」
我們加了 Facebook 好友很久,但一直沒有說過話。當時剛開始做播客,勁頭十足,聽說是友台主播,自然很快勾搭起來。那天,他和我分享了許多對播客行業觀察:「中文播客太簡單了,都是談話類節目」、「我和許多人聊,感覺大家對音頻都還不大了解,甚至在平台工作的人了解都不多」……即便只是線上閑談,也感受得到他對這個行業的熱情,同時,他也做了不少努力——為某公司製作了一檔品牌播客,也開始了一份叫《播客一下》(Just Pod)的行業通訊。
這麼有熱情,為什麼不全職做?當時,剛好錄完《世上無難事,只要肯放棄》那期節目,於是變身職業勸退師,慫恿他辭職創業,把自己喜歡的事變成工作。但他很坦率地說,這個市場在中國才剛剛起步,純靠做播客的收入,很難養活自己。
不過,這半年情況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楊一和朋友已經成立了一間播客廣告公司;又接受了 BBC、紐約時報和第一財經的訪問,而在這篇和播客界最有名的行業通訊 Hot Pod 的訪談中,他更詳細闡述了中文播客的歷史和現狀,也分享了自己對行業未來發展的看法。如果你想了解中文播客,這是一篇不可不讀的好材料。
7月21日,人類登月50年的日子,楊一結束了在前單位長達8年的工作,接下來將全職投入播客事業。我想,中文播客離「Serial 時刻」的到來又近了一點點。
本文首發於 Hot Pod,作者 Nicholas Quah,中文版由楊一和我共同翻譯,經楊一審定後刊發
我天然地就對中國有興趣,部分原因是我一向對那些和我長得很像的人在做什麼感到好奇(譯者註:作者 Nicholas Quah 為馬來西亞華人),但主要還是因為,某種程度上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它的策略總是會無可避免地影響到你。
播客,以及更廣泛的點播音頻行業也不例外。你可能已經注意到了,但在最近的幾個月,在播客行業的一些領域、以及風險投資界,似乎對中國播客可以為美國市場帶來什麼經驗與教訓,特別是在商業模式方面,顯得越來越有興趣。
這種興趣似乎很大程度上是由去年9月 Marketplace(譯者註:由美國的公共廣播機構 American Public Media 製作的一檔財經類節目)的一篇報道引發的。這篇報道中提到中國強勁的「錯失恐懼」(Fear of missing out, FOMO)產業或者說滿足自我提升焦慮的經濟,其價值去年估計有約73億美元。而對這一產業至關重要的,是「付費音頻」這部分業務,這類產品主要出現在一些大型音頻平台上,其中最大的平台是喜馬拉雅 FM。(有些讀者可能熟悉這個名字,因為它是 Himalaya Media 的主要投資者。今年早些時候,這家播客初創公司在沒有多少現有業務的情況下籌集了1億美元資金,引起了一些媒體的注意)無論如何,Marketplace 的這篇報道用「播客」這個詞來形容這一健康的付費音頻業務,而且這一概念似乎一直沿用至今。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大型風險投資公司 Andreessen Horowitz 以喜馬拉雅 FM 作為案例,在最近的博客文章中被重點分析,這家風投公司在播客行業中提出了自己的投資理論。
我過去陸陸續續寫過一些有關中國播客的文章,但我覺得像 Marketplace 的報道那樣使用「播客」一詞(譯者註:來形容中國的整個音頻生態),本質上是用詞不當。要是有人試圖將喜馬拉雅 FM 所主導的中國音頻市場的規模和美國的播客產業相比,則是一種更加需要警惕地錯配。準確的比較應該要包括美國的播客產業、有聲讀物、冥想類應用程序,以及未來的 Spotify 。這不是要否定任何從中國音頻市場為美國的播客或音頻行業汲取經驗教訓的努力,肯定有很多東西值得學習。我只是說我們應該非常明確我們探討的對象是什麼,我們要汲取什麼。
不論怎樣,以上只是我對這件事問題的看法,而我只是一個在美國康涅狄格州寫博客的人。所以我想我需要接觸到一位身處中國播客行業中的人,於是我想到了楊一。楊一住在上海,他在一家類似於 CNBC 的財經電視頻道擔任責任編輯(註:楊一已於2019年7月離開電視工作,全職從事播客領域的工作);另一方面,他運營着一些與播客相關的項目,包括一檔名叫《忽左忽右》的播客,一個叫「PodFest China」的播客行業活動,以及一份名叫《播客一下》(Just Pod),類似 HotPod 的有關播客行業的中文通訊。我們認識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把一些問題發給了楊一,他非常友善,並給了我很深入的回答。
在進入問答環節之前,我們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數據速覽:喜馬拉雅 FM 自稱它的應用程序下載量超過5.4億次。我再引述《華爾街見聞》2018年的一篇文章,其中來自喜馬拉雅的內部人士稱,喜馬拉雅的日活用戶接近4000萬。如果你關注這些數據,可以小本本記一筆。
雖然中美的音頻市場之間存在重大差異,但潛在的動力卻有許多相似之處。事實上,人們能感覺到,核心上的差異源於一個歷史性的分化:一個市場(中國)中出現非常活躍的、佔主導地位的平台已經有一段時間了,而另一個市場(美國)還沒有。
還有一件事你也應該注意:「播客」這個詞的核心矛盾。人們很容易認為這是翻譯過程中產生的某種理解上的誤差,但在美國,你也可以看到同樣模糊概念的現象出現(去看看 Luminary 就知道)。
Nicholas Quah 按:為了閱讀流暢,我已經濃縮、編輯和簡化了楊一的回答,為了留出空間,我不得不捨棄一些東西。你還應該記住,以下問答只代表一個人對複雜系統的解釋,而且這個承載了許多內容。我相信中國播客還有很多其他方面沒有在此表現出來,希望未來我們有機會來展現這些方面。
我還想對我的父親大喊一聲,因為他一直堅持認為中國總有一天會和我的工作聯繫起來。
好了,讓我們進入我和來自上海的《播客一下》的創辦者楊一的問答。
Hot Pod:您認為北美人是如何看待中國播客的?您對這些觀點有什麼看法?
楊一:當我和我的西方朋友談到中國播客的時候,我感覺,第一個跳入他們腦海的概念是「知識付費」。我猜想這種認知可能主要來自去年 Marketplace 的那篇報道。這篇報道向西方讀者提供了有關中國音頻市場、它背後的市場規模,以及造就這一現象的社會環境的某種解讀。
但是我必須說,把「知識付費」等同於「播客」,或者認為「知識付費」是一種在中國「很流行的播客」,是一種誤解。我覺得「知識付費」和「播客」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我個人將「知識付費」看作是在線教育的一部分——它更類似於「慕課」(MOOC,即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的英文縮寫)這樣的在線公開課程,而不是對「付費播客」或者「播客界的 Netflix」模式這些想法的一種回應。
當然,在「知識付費」的體系之外,在中國也有所謂的「獨立播客」。我看到一些西方媒體試圖描述這一現象,討論這些獨立播客如何發揮這一媒介天然的開放屬性,去報道一些「主流媒體沒有涉及的話題」。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現象確實存在,但並非主流。的確,中國的播客表現出一些所謂「獨立」的氣質,但我認為它不同於西方價值觀中所理解的「獨立」。它不是一種價值觀上的「反叛」,而更多的是由於內容的多樣性和節目製作的業餘水平,而帶來的某種「自然」的活力。
我必須要強調,語言很多時候的確是阻礙不同國家的播客圈彼此了解的一個障礙。所以如果你僅僅只讀了幾篇英文報道,就試圖定義「中文播客」,甚至認為它們反映了中文播客的全貌,這毫無疑問是一種從英語視角出發的偏見。當英文媒體寫下有關中文播客的故事時,這些報道背後的記者和編輯,通常選擇的是那些最特殊、也最有趣的故事,這些個案或許很有意思,但它一定不能反映中文播客的全部。
Hot Pod:您能否簡要介紹一下中國的播客或者更寬泛一點的,在線點播音頻的歷史?

楊一:如果我們把2004年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的 Ben Hammersley 所撰寫的有關播客的專欄文章,視作「播客」的某種起點。那麼在中文世界,播客出現得非常早。最早的一批中文播客在那時就已經出現了,其中名叫「反波」的播客節目更獲得了2005年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國際博客大賽(The Bobs)的最佳中文播客。但在當時聽播客的人非常少。儘管如此,仍然有些有趣的地方值得注意,中文播客與英文播客差不多同時起步,中文播客主與英文播客主在當時也面臨著相同的問題。他們需要為自己的播客尋找託管服務器,需要製作自己的 RSS 訂閱源,然後他們還需要提交給蘋果,以便讓他們的播客節目出現在 iTunes 上。
接着,到了2012年前後,一些大型的本土音頻平台開始出現,比如喜馬拉雅 FM。在中國,「音頻平台」所扮演的角色,我覺得在西方世界似乎到目前為止還沒出現過。在美國,託管音頻的主機服務、節目分發渠道和給用戶使用的訂閱 RSS 的應用程序是完全分開的。但是在中國,像喜馬拉雅 FM 這樣的音頻平台,將這些功能都聚合在一起,讓它看起來更像一個音頻版的 YouTube。
當然,即使有這樣的服務,播主還是可以選擇使用自己的服務器,製作自己的 RSS 訂閱源,來讓你的播客出現在網上。但在實際操作層面,這些仍然要求一定的技術能力,並不是每一個播主都能順利完成這一系列操作。更重要的是,在中國要合法地搭建網站和服務器,需要得到當地公安機關或者互聯網主管部門的批准。如果不想這麼麻煩,你就要去選擇海外服務器,但就會始終面臨無法訪問的風險,你的聽眾可能一夜之間就無法收聽你的任何節目。所以選擇一個易於使用又提供一站式服務的音頻平台,對於很多播主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然這種一站式服務仍有讓人煩惱之處。比如,音頻平台可以在你上傳的節目中插入廣告,卻不會像 YouTube 跟上傳者分成那樣跟播客主分成。另外顯而易見的是,你的節目很可能因為受到審查而被平台刪除。有些播主為了方便只能忍受這些煩惱,但另外一些人則不願妥協,於是他們會重新選擇使用自己的服務器來託管節目。
此外,中國消費者現在更習慣使用這些大型的音頻平台來收聽各種在線點播的音頻內容。如果你的播客不在這些平台發布,意味着你將失去一個輕鬆地接觸到更廣大受眾的機會。又因為整個音頻市場都由少數幾家平台主導,它們自然對如何形塑整個市場有更大的話語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平台可以決定什麼樣的節目能夠被推薦。事實上在中國,音頻平台本身也會製作節目——「知識付費」內容就是其中一種,這就很像 Luminary 現在在做的事情。
儘管在自己的應用程序里已經有很多第三方的內容,但平台更關注的還是自己製作的獨家內容。中國播客目前的困境就像是,如果美國從2012年起就出現了一個成功的 Luminary。這就拋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如果 Luminary 在《Serial》(譯者註:美國一檔真實犯罪類播客節目,在2014年開播之後,引發廣泛討論,並直接推動美國播客產業出現了一次爆發,可參見《播客一下》第一期)之前出現,Spotify 也在《Serial》開播之前就開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播客上,那麼今天美國的播客市場將是一幅怎樣的圖景。在我看來,Hot Pod 之前提到的,美國播客圈如今對於平台力量的許多擔憂,事實上已經困擾了中國播客圈多年。在這個層面上,美國播客圈此刻可能會與我們產生某種共鳴。

在我的理解中,西方播客世界一直秉持着 Web 2.0 時代的某些精神——自由、開放、共享的網絡空間等等,這通常被形容為互聯網的「去中心化」。換句話說,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平台能夠控制這個開放的播客環境。而中國的音頻市場從2012年喜馬拉雅 FM 的出現開始,就處於「平台中心化」的環境。意味着平台的喜好決定着什麼樣的節目能夠獲得推薦的機會,平台自身的發展戰略決定着什麼樣的商業模式能夠得到更多的支持。這些發展戰略在驅動了整個市場。幾年前,主要的幾家音頻平台發現,那種為播主提供託管服務,然後再依靠這些用戶原創內容所帶來的流量換取廣告的模式並不可行(總的來說,音頻在中國遠沒有視頻火)。所以它們開始嘗試新的商業模式,「知識付費」就是這些嘗試中成功的一個。儘管喜馬拉雅 FM 以其建立在訂閱基礎上的「知識付費」業務而聞名,但不太為西方人所熟知的是,它還是中國最大的有聲讀物分銷商,它獲得了市場上70%有聲讀物的授權因而接近於壟斷地位。這意味着,喜馬拉雅FM在中國不僅是一個音頻版的 YouTube,它還是一個中國版的 Audible。
在很多人的觀念中,「播客」與「音頻」的區別並沒有那麼清晰。這就是為什麼當很多人說「中國的音頻市場正在蓬勃發展」的時候,它們其實想到的是「知識付費」、有聲書或者其他音頻內容,而不是「播客」。相對的在美國,將「播客」視為一個單獨的媒介已經成為市場共識。而中國的這種「混為一談」,毫無疑問會影響播客的發展,它會讓市場始終無法清晰地認識到播客的價值。
Hot Pod:您會如何描述中文播客的製作文化?
楊一:如果要我總結中國播客節目最大的特點,我會說是「業餘製作」。
你也許剛剛讀到過《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有關《故事 FM》的報道,像《故事 FM》這樣由專業的製作團隊生產的節目,在中文播客界可謂鳳毛麟角。事實上,大多數中文播客主在製作自己的播客前,沒有任何的媒體從業經驗或者音頻製作經驗。製作人或者主持人也視播客為副業或者業餘愛好,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有全職工作,僅僅利用周末等業餘時間來製作播客,因為播客還無法給他們帶來穩定的收入。這令許多的中文播客聽起來仍然留有早期「音頻博客」(Audio Blogging)的痕迹,而且節目的定期更新和持續運營對運營者來說都是挑戰。
我想你可以這樣描述在中國的大多數「業餘製作」:形式上「同質化」——大多數都是「聊天節目」(Chat Cast)的形式,也就是單人獨白或是脫口秀;但在內容上「多樣化」,很多播客的製作人儘管沒有媒體從業經驗,但常常是某個領域的專家,他們的節目也會圍繞這個自己熟悉的專業領域展開。我很喜歡舉《博物志》的例子。這個播客的主題就是博物館,它的主持人兼製作人婉瑩,畢業於加拿大一所大學的博物館學。她從2016年起與搭檔開辦了這個節目,在過去的三年里,她們持續製作出的節目吸引了一群非常忠實的粉絲,從而形成了一個社群。目前,這個播客能依靠聽眾捐款來維持運營。除此之外還有,探討用戶交互界面設計的播客《Anyway FM》,以談論自由職業為主題的播客《無業游民》等,它們都定位在特定的細分領域,或者用中國互聯網界很喜歡的說法叫「內容垂直」。
我認為這種以聊天節目為主導的內容同質化和中文播客主們缺乏音頻製作經驗有關,但造成這樣的局面,或許也和中國廣播事業的發展歷史密切相關。
文革之後,廣播電台在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了一場改革。臨近香港的、華南地區的電台在這場改革中起到了領軍作用。他們從香港的電台那裡學會了做現場直播,主持人不再需要像以往那樣,要嚴格按照事先被核准過的腳本錄製節目,而是可以在兩到三個小時的節目時段里,自由組合音樂、新聞資訊、交通信息和天氣預報等多種內容,用更像日常交談的方式來主持。並且,有的節目也會讓聽眾打電話進來,和主持人或嘉賓即時對話。
儘管中國的廣播電台是國有的,但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它們的收入方式由政府撥款,轉向商業廣告。中國從來沒有過像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或英國廣播公司(BBC)這樣的公共廣播系統,所以每個電台都要自負盈虧。在這樣的情況下,對電台來說取得商業上的成功是最重要的,而談話節目的形式則具有巨大的商業價值——除了主持人的薪資意外,它在製作上幾乎不用花費任何成本,但可以帶來相當可觀的收入。例如,一家上海的流行音樂電台,在早高峰時期的廣告就能帶來1億元人民幣(約合1400萬美元)的年收入。
在這樣的環境下,廣播電台幾乎沒有動力去製作成本更高或需要耗費更多人力和時間來製作的節目。當然,如果純粹從商業的角度出發,這樣的做法並沒有錯,但我認為這也導致了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 來自廣播電台的音頻製作人幾乎沒有製作敘事類節目(Storytelling Programs)的經驗。
Hot Pod:你認為中文播客的發展方向是怎麼樣的?
楊一:在中國很難做全面的播客市場調查,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播客和其他音頻內容主要集中在喜馬拉雅 FM、蜻蜓、荔枝等少數幾個主要音頻平台上,而它們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這也使得它們將自己的數據視為非常有價值的資產。此外,他們都不是上市公司,因此也沒有義務向公眾披露自己的數據。如果一家諮詢公司想要做一個調查,它就必須與這些音頻平台合作,以獲得調查所需要的數據。這種合作又會使得研究本身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偏見,從而無法準確反映播客產業的整體圖景。
我認為,播客在中國還遠遠沒有大眾化。大多數播客的團隊規模很小,受眾也非常有限,很難吸引到廣告商。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我之前也有提到,例如,大多數現有的播客都是業餘製作的,這使得節目的更新頻率很不穩定,節目的質量層次不齊,遠不如視頻媒介那樣專業化,這也使得廣告商在權衡是否在音頻節目中投放廣告時猶豫不決;另一方面,在缺乏廣告收入的情況下,播客主又無法將「播客」當成職業來看待,因為無法帶來穩定的收入,這反過來就讓播客的製作繼續維持在某種業餘愛好的水平。最終無法帶來播客製作水平從業餘向專業的轉變。這讓播客行業也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
而從音頻平台的角度來看,他們依靠「知識付費」或者訂戶帶來的收入,因而將繼續投入在這些自有節目的製作上。音頻平台似乎也不會理由慷慨地將這些收入送給播客主,以提升播客節目的質量。客觀上,這將讓播客與「知識付費」的競爭變得更加艱難。
當前的中國播客市場更像是美國在《Serial》出現前的狀況:有一些愛好者參與其中,但並沒有引發大眾的廣泛關注,也沒有讓市場注意到它潛在的商業價值。播客的商業化在中國還處在一片混沌之中。
中國播客什麼時候才會迎來「Serial 時刻」?或者這個市場的貨幣化並不是由一檔現象級節目來觸發,那麼又將是什麼樣的契機能夠吸引資本,甚至是投資者進入這個領域?現在還沒有一個清晰的線索。
在我看來,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製作高水準的播客。我相信,只有播客製作水準的普遍提升,才能夠促進中國的「Serial 時刻」儘快到來。
我對中文播客的前景仍然相當樂觀,一方面,中國14億人的龐大市場和人均收入與消費能力的提高,為娛樂消費創造了巨大潛能,而且有越來越多人開始有了「聽」的習慣;另一方面,我也能夠感受到有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到中國的播客市場,這也會促使各方力量去挖掘播客的商業潛能;而中文播客行業自身也在行動起來,讓自己變得專業化、行業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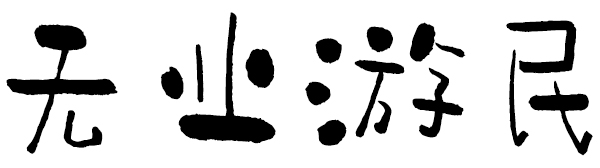
文章能簡繁轉換,真細心
如果能知道哪些內容受歡迎,哪些稀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