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在开始这个播客后没多久,就收到了杨一在 Facebook 上传来的信息:「Hello!可以和友台主播认识一下吗?」
我们加了 Facebook 好友很久,但一直没有说过话。当时刚开始做播客,劲头十足,听说是友台主播,自然很快勾搭起来。那天,他和我分享了许多对播客行业观察:「中文播客太简单了,都是谈话类节目」、「我和许多人聊,感觉大家对音频都还不大了解,甚至在平台工作的人了解都不多」……即便只是线上闲谈,也感受得到他对这个行业的热情,同时,他也做了不少努力——为某公司制作了一档品牌播客,也开始了一份叫《播客一下》(Just Pod)的行业通讯。
这么有热情,为什么不全职做?当时,刚好录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那期节目,于是变身职业劝退师,怂恿他辞职创业,把自己喜欢的事变成工作。但他很坦率地说,这个市场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纯靠做播客的收入,很难养活自己。
不过,这半年情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杨一和朋友已经成立了一间播客广告公司;又接受了 BBC、纽约时报和第一财经的访问,而在这篇和播客界最有名的行业通讯 Hot Pod 的访谈中,他更详细阐述了中文播客的历史和现状,也分享了自己对行业未来发展的看法。如果你想了解中文播客,这是一篇不可不读的好材料。
7月21日,人类登月50年的日子,杨一结束了在前单位长达8年的工作,接下来将全职投入播客事业。我想,中文播客离「Serial 时刻」的到来又近了一点点。
本文首发于 Hot Pod,作者 Nicholas Quah,中文版由杨一和我共同翻译,经杨一审定后刊发
我天然地就对中国有兴趣,部分原因是我一向对那些和我长得很像的人在做什么感到好奇(译者注:作者 Nicholas Quah 为马来西亚华人),但主要还是因为,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它的策略总是会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你。
播客,以及更广泛的点播音频行业也不例外。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但在最近的几个月,在播客行业的一些领域、以及风险投资界,似乎对中国播客可以为美国市场带来什么经验与教训,特别是在商业模式方面,显得越来越有兴趣。
这种兴趣似乎很大程度上是由去年9月 Marketplace(译者注:由美国的公共广播机构 American Public Media 制作的一档财经类节目)的一篇报道引发的。这篇报道中提到中国强劲的「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 FOMO)产业或者说满足自我提升焦虑的经济,其价值去年估计有约73亿美元。而对这一产业至关重要的,是「付费音频」这部分业务,这类产品主要出现在一些大型音频平台上,其中最大的平台是喜马拉雅 FM。(有些读者可能熟悉这个名字,因为它是 Himalaya Media 的主要投资者。今年早些时候,这家播客初创公司在没有多少现有业务的情况下筹集了1亿美元资金,引起了一些媒体的注意)无论如何,Marketplace 的这篇报道用「播客」这个词来形容这一健康的付费音频业务,而且这一概念似乎一直沿用至今。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大型风险投资公司 Andreessen Horowitz 以喜马拉雅 FM 作为案例,在最近的博客文章中被重点分析,这家风投公司在播客行业中提出了自己的投资理论。
我过去陆陆续续写过一些有关中国播客的文章,但我觉得像 Marketplace 的报道那样使用「播客」一词(译者注:来形容中国的整个音频生态),本质上是用词不当。要是有人试图将喜马拉雅 FM 所主导的中国音频市场的规模和美国的播客产业相比,则是一种更加需要警惕地错配。准确的比较应该要包括美国的播客产业、有声读物、冥想类应用程序,以及未来的 Spotify 。这不是要否定任何从中国音频市场为美国的播客或音频行业汲取经验教训的努力,肯定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我只是说我们应该非常明确我们探讨的对象是什么,我们要汲取什么。
不论怎样,以上只是我对这件事问题的看法,而我只是一个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写博客的人。所以我想我需要接触到一位身处中国播客行业中的人,于是我想到了杨一。杨一住在上海,他在一家类似于 CNBC 的财经电视频道担任责任编辑(注:杨一已于2019年7月离开电视工作,全职从事播客领域的工作);另一方面,他运营着一些与播客相关的项目,包括一档名叫《忽左忽右》的播客,一个叫「PodFest China」的播客行业活动,以及一份名叫《播客一下》(Just Pod),类似 HotPod 的有关播客行业的中文通讯。我们认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把一些问题发给了杨一,他非常友善,并给了我很深入的回答。
在进入问答环节之前,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数据速览:喜马拉雅 FM 自称它的应用程序下载量超过5.4亿次。我再引述《华尔街见闻》2018年的一篇文章,其中来自喜马拉雅的内部人士称,喜马拉雅的日活用户接近4000万。如果你关注这些数据,可以小本本记一笔。
虽然中美的音频市场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但潜在的动力却有许多相似之处。事实上,人们能感觉到,核心上的差异源于一个历史性的分化:一个市场(中国)中出现非常活跃的、占主导地位的平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另一个市场(美国)还没有。
还有一件事你也应该注意:「播客」这个词的核心矛盾。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翻译过程中产生的某种理解上的误差,但在美国,你也可以看到同样模糊概念的现象出现(去看看 Luminary 就知道)。
Nicholas Quah 按:为了阅读流畅,我已经浓缩、编辑和简化了杨一的回答,为了留出空间,我不得不舍弃一些东西。你还应该记住,以下问答只代表一个人对复杂系统的解释,而且这个承载了许多内容。我相信中国播客还有很多其他方面没有在此表现出来,希望未来我们有机会来展现这些方面。
我还想对我的父亲大喊一声,因为他一直坚持认为中国总有一天会和我的工作联系起来。
好了,让我们进入我和来自上海的《播客一下》的创办者杨一的问答。
Hot Pod:您认为北美人是如何看待中国播客的?您对这些观点有什么看法?
杨一:当我和我的西方朋友谈到中国播客的时候,我感觉,第一个跳入他们脑海的概念是「知识付费」。我猜想这种认知可能主要来自去年 Marketplace 的那篇报道。这篇报道向西方读者提供了有关中国音频市场、它背后的市场规模,以及造就这一现象的社会环境的某种解读。
但是我必须说,把「知识付费」等同于「播客」,或者认为「知识付费」是一种在中国「很流行的播客」,是一种误解。我觉得「知识付费」和「播客」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个人将「知识付费」看作是在线教育的一部分——它更类似于「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的英文缩写)这样的在线公开课程,而不是对「付费播客」或者「播客界的 Netflix」模式这些想法的一种回应。
当然,在「知识付费」的体系之外,在中国也有所谓的「独立播客」。我看到一些西方媒体试图描述这一现象,讨论这些独立播客如何发挥这一媒介天然的开放属性,去报道一些「主流媒体没有涉及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并非主流。的确,中国的播客表现出一些所谓「独立」的气质,但我认为它不同于西方价值观中所理解的「独立」。它不是一种价值观上的「反叛」,而更多的是由于内容的多样性和节目制作的业余水平,而带来的某种「自然」的活力。
我必须要强调,语言很多时候的确是阻碍不同国家的播客圈彼此了解的一个障碍。所以如果你仅仅只读了几篇英文报道,就试图定义「中文播客」,甚至认为它们反映了中文播客的全貌,这毫无疑问是一种从英语视角出发的偏见。当英文媒体写下有关中文播客的故事时,这些报道背后的记者和编辑,通常选择的是那些最特殊、也最有趣的故事,这些个案或许很有意思,但它一定不能反映中文播客的全部。
Hot Pod: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中国的播客或者更宽泛一点的,在线点播音频的历史?

杨一:如果我们把2004年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的 Ben Hammersley 所撰写的有关播客的专栏文章,视作「播客」的某种起点。那么在中文世界,播客出现得非常早。最早的一批中文播客在那时就已经出现了,其中名叫「反波」的播客节目更获得了2005年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国际博客大赛(The Bobs)的最佳中文播客。但在当时听播客的人非常少。尽管如此,仍然有些有趣的地方值得注意,中文播客与英文播客差不多同时起步,中文播客主与英文播客主在当时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他们需要为自己的播客寻找托管服务器,需要制作自己的 RSS 订阅源,然后他们还需要提交给苹果,以便让他们的播客节目出现在 iTunes 上。
接着,到了2012年前后,一些大型的本土音频平台开始出现,比如喜马拉雅 FM。在中国,「音频平台」所扮演的角色,我觉得在西方世界似乎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过。在美国,托管音频的主机服务、节目分发渠道和给用户使用的订阅 RSS 的应用程序是完全分开的。但是在中国,像喜马拉雅 FM 这样的音频平台,将这些功能都聚合在一起,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个音频版的 YouTube。
当然,即使有这样的服务,播主还是可以选择使用自己的服务器,制作自己的 RSS 订阅源,来让你的播客出现在网上。但在实际操作层面,这些仍然要求一定的技术能力,并不是每一个播主都能顺利完成这一系列操作。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要合法地搭建网站和服务器,需要得到当地公安机关或者互联网主管部门的批准。如果不想这么麻烦,你就要去选择海外服务器,但就会始终面临无法访问的风险,你的听众可能一夜之间就无法收听你的任何节目。所以选择一个易于使用又提供一站式服务的音频平台,对于很多播主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这种一站式服务仍有让人烦恼之处。比如,音频平台可以在你上传的节目中插入广告,却不会像 YouTube 跟上传者分成那样跟播客主分成。另外显而易见的是,你的节目很可能因为受到审查而被平台删除。有些播主为了方便只能忍受这些烦恼,但另外一些人则不愿妥协,于是他们会重新选择使用自己的服务器来托管节目。
此外,中国消费者现在更习惯使用这些大型的音频平台来收听各种在线点播的音频内容。如果你的播客不在这些平台发布,意味着你将失去一个轻松地接触到更广大受众的机会。又因为整个音频市场都由少数几家平台主导,它们自然对如何形塑整个市场有更大的话语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平台可以决定什么样的节目能够被推荐。事实上在中国,音频平台本身也会制作节目——「知识付费」内容就是其中一种,这就很像 Luminary 现在在做的事情。
尽管在自己的应用程序里已经有很多第三方的内容,但平台更关注的还是自己制作的独家内容。中国播客目前的困境就像是,如果美国从2012年起就出现了一个成功的 Luminary。这就抛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 Luminary 在《Serial》(译者注:美国一档真实犯罪类播客节目,在2014年开播之后,引发广泛讨论,并直接推动美国播客产业出现了一次爆发,可参见《播客一下》第一期)之前出现,Spotify 也在《Serial》开播之前就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播客上,那么今天美国的播客市场将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在我看来,Hot Pod 之前提到的,美国播客圈如今对于平台力量的许多担忧,事实上已经困扰了中国播客圈多年。在这个层面上,美国播客圈此刻可能会与我们产生某种共鸣。

在我的理解中,西方播客世界一直秉持着 Web 2.0 时代的某些精神——自由、开放、共享的网络空间等等,这通常被形容为互联网的「去中心化」。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平台能够控制这个开放的播客环境。而中国的音频市场从2012年喜马拉雅 FM 的出现开始,就处于「平台中心化」的环境。意味着平台的喜好决定着什么样的节目能够获得推荐的机会,平台自身的发展战略决定着什么样的商业模式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这些发展战略在驱动了整个市场。几年前,主要的几家音频平台发现,那种为播主提供托管服务,然后再依靠这些用户原创内容所带来的流量换取广告的模式并不可行(总的来说,音频在中国远没有视频火)。所以它们开始尝试新的商业模式,「知识付费」就是这些尝试中成功的一个。尽管喜马拉雅 FM 以其建立在订阅基础上的「知识付费」业务而闻名,但不太为西方人所熟知的是,它还是中国最大的有声读物分销商,它获得了市场上70%有声读物的授权因而接近于垄断地位。这意味着,喜马拉雅FM在中国不仅是一个音频版的 YouTube,它还是一个中国版的 Audible。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播客」与「音频」的区别并没有那么清晰。这就是为什么当很多人说「中国的音频市场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它们其实想到的是「知识付费」、有声书或者其他音频内容,而不是「播客」。相对的在美国,将「播客」视为一个单独的媒介已经成为市场共识。而中国的这种「混为一谈」,毫无疑问会影响播客的发展,它会让市场始终无法清晰地认识到播客的价值。
Hot Pod:您会如何描述中文播客的制作文化?
杨一:如果要我总结中国播客节目最大的特点,我会说是「业余制作」。
你也许刚刚读到过《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有关《故事 FM》的报道,像《故事 FM》这样由专业的制作团队生产的节目,在中文播客界可谓凤毛麟角。事实上,大多数中文播客主在制作自己的播客前,没有任何的媒体从业经验或者音频制作经验。制作人或者主持人也视播客为副业或者业余爱好,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全职工作,仅仅利用周末等业余时间来制作播客,因为播客还无法给他们带来稳定的收入。这令许多的中文播客听起来仍然留有早期「音频博客」(Audio Blogging)的痕迹,而且节目的定期更新和持续运营对运营者来说都是挑战。
我想你可以这样描述在中国的大多数「业余制作」:形式上「同质化」——大多数都是「聊天节目」(Chat Cast)的形式,也就是单人独白或是脱口秀;但在内容上「多样化」,很多播客的制作人尽管没有媒体从业经验,但常常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的节目也会围绕这个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展开。我很喜欢举《博物志》的例子。这个播客的主题就是博物馆,它的主持人兼制作人婉莹,毕业于加拿大一所大学的博物馆学。她从2016年起与搭档开办了这个节目,在过去的三年里,她们持续制作出的节目吸引了一群非常忠实的粉丝,从而形成了一个社群。目前,这个播客能依靠听众捐款来维持运营。除此之外还有,探讨用户交互界面设计的播客《Anyway FM》,以谈论自由职业为主题的播客《无业游民》等,它们都定位在特定的细分领域,或者用中国互联网界很喜欢的说法叫「内容垂直」。
我认为这种以聊天节目为主导的内容同质化和中文播客主们缺乏音频制作经验有关,但造成这样的局面,或许也和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
文革之后,广播电台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了一场改革。临近香港的、华南地区的电台在这场改革中起到了领军作用。他们从香港的电台那里学会了做现场直播,主持人不再需要像以往那样,要严格按照事先被核准过的脚本录制节目,而是可以在两到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里,自由组合音乐、新闻资讯、交通信息和天气预报等多种内容,用更像日常交谈的方式来主持。并且,有的节目也会让听众打电话进来,和主持人或嘉宾即时对话。
尽管中国的广播电台是国有的,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它们的收入方式由政府拨款,转向商业广告。中国从来没有过像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或英国广播公司(BBC)这样的公共广播系统,所以每个电台都要自负盈亏。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电台来说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是最重要的,而谈话节目的形式则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除了主持人的薪资意外,它在制作上几乎不用花费任何成本,但可以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例如,一家上海的流行音乐电台,在早高峰时期的广告就能带来1亿元人民币(约合1400万美元)的年收入。
在这样的环境下,广播电台几乎没有动力去制作成本更高或需要耗费更多人力和时间来制作的节目。当然,如果纯粹从商业的角度出发,这样的做法并没有错,但我认为这也导致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来自广播电台的音频制作人几乎没有制作叙事类节目(Storytelling Programs)的经验。
Hot Pod:你认为中文播客的发展方向是怎么样的?
杨一:在中国很难做全面的播客市场调查,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播客和其他音频内容主要集中在喜马拉雅 FM、蜻蜓、荔枝等少数几个主要音频平台上,而它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也使得它们将自己的数据视为非常有价值的资产。此外,他们都不是上市公司,因此也没有义务向公众披露自己的数据。如果一家咨询公司想要做一个调查,它就必须与这些音频平台合作,以获得调查所需要的数据。这种合作又会使得研究本身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偏见,从而无法准确反映播客产业的整体图景。
我认为,播客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大众化。大多数播客的团队规模很小,受众也非常有限,很难吸引到广告商。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之前也有提到,例如,大多数现有的播客都是业余制作的,这使得节目的更新频率很不稳定,节目的质量层次不齐,远不如视频媒介那样专业化,这也使得广告商在权衡是否在音频节目中投放广告时犹豫不决;另一方面,在缺乏广告收入的情况下,播客主又无法将「播客」当成职业来看待,因为无法带来稳定的收入,这反过来就让播客的制作继续维持在某种业余爱好的水平。最终无法带来播客制作水平从业余向专业的转变。这让播客行业也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而从音频平台的角度来看,他们依靠「知识付费」或者订户带来的收入,因而将继续投入在这些自有节目的制作上。音频平台似乎也不会理由慷慨地将这些收入送给播客主,以提升播客节目的质量。客观上,这将让播客与「知识付费」的竞争变得更加艰难。
当前的中国播客市场更像是美国在《Serial》出现前的状况:有一些爱好者参与其中,但并没有引发大众的广泛关注,也没有让市场注意到它潜在的商业价值。播客的商业化在中国还处在一片混沌之中。
中国播客什么时候才会迎来「Serial 时刻」?或者这个市场的货币化并不是由一档现象级节目来触发,那么又将是什么样的契机能够吸引资本,甚至是投资者进入这个领域?现在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线索。
在我看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制作高水准的播客。我相信,只有播客制作水准的普遍提升,才能够促进中国的「Serial 时刻」尽快到来。
我对中文播客的前景仍然相当乐观,一方面,中国14亿人的庞大市场和人均收入与消费能力的提高,为娱乐消费创造了巨大潜能,而且有越来越多人开始有了「听」的习惯;另一方面,我也能够感受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中国的播客市场,这也会促使各方力量去挖掘播客的商业潜能;而中文播客行业自身也在行动起来,让自己变得专业化、行业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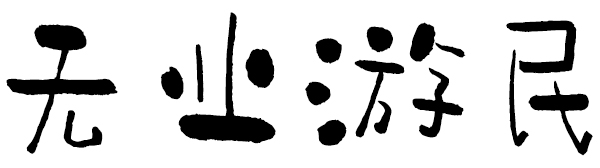
文章能简繁转换,真细心
如果能知道哪些内容受欢迎,哪些稀缺就好了。